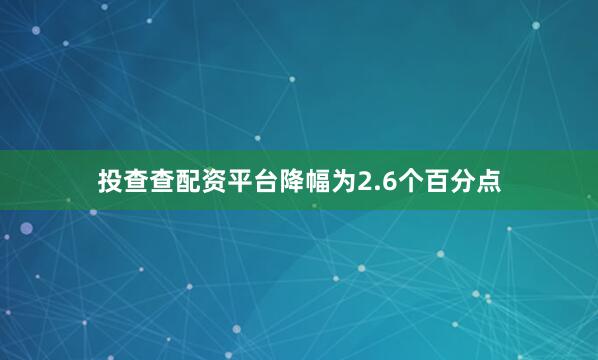股票免费配资而是输在了极度的“水土不服”

想象一下这个画面:曾经在欧亚大陆上像推土机一样横扫千军的蒙古骑兵,这会儿正陷在越南的烂泥地里。
战马焦躁地刨着蹄子,蚊虫乌云般围着人畜叮咬,盔甲里的衬衣早就被汗水、雨水沤得发臭。
抬头望去,是遮天蔽日的热带丛林,藤蔓像巨蟒一样缠绕着参天古树,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。“长生天”的骄子们,第一次对着这片闷热、潮湿、陌生的土地,感到了深入骨髓的无力。横扫了半个地球,怎么就死活啃不下越南这块“硬骨头”?
晚年的忽必烈,据说捶着龙椅叹气,肠子都悔青了,早知道,真该多听听岭南人的话!
无敌铁骑的“水土不服”综合征
蒙古军队的厉害,地球人都知道。人家打仗就三板斧,但招招致命:跑得快(骑兵机动)、射得准(骑射无双)、压得狠(重兵集团冲击)。靠着这看家本领,他们从蒙古高原一路打到多瑙河,灭国无数,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。
展开剩余93%可这三板斧,到了越南,就像砸在棉花上,威力大打折扣,甚至反过来成了累赘。
第一斧:跑得快?跑不动! 越南那地方,跟蒙古老家的大草原和中原的平原完全是两个世界。河网密布,稻田纵横,山高林密。
蒙古骑兵最依赖的战马,在这种地方彻底抓瞎。烂泥地陷马蹄,稻田水沟挡道,茂密的丛林更是连马头都转不过来。骑兵冲不起来,威力直接废掉七成。别说冲锋陷阵了,行军都成了噩梦。
后勤补给线长得吓人,又容易被熟悉地形的越南游击队(那时候叫“义军”)神出鬼没地切断。蒙古兵饿着肚子在泥水里挣扎,哪还有力气打仗?
第二斧:射得准?看不见! 蒙古骑兵的看家本领是骑射。在开阔地,万箭齐发,箭如雨下,敌人还没靠近就被射成刺猬。
可在越南的热带丛林和崎岖山地里,这招也失灵了。树木藤蔓遮挡视线,根本找不到开阔的射击角度。越南军队聪明得很,就跟你玩丛林游击战。他们熟悉每一片林子,每一条小路,利用复杂地形跟你捉迷藏。
蒙古兵追进去,往往连人影都瞄不到,反而冷不丁就被埋伏的冷箭、竹签陷阱放倒一片。有力气没处使,憋屈得要命。
第三斧:压得狠?压不住! 蒙古人打仗,喜欢集中优势兵力,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压垮对手。但在越南,这招也遇到了克星。越南人深知硬拼是找死,他们的策略非常明确:你大军来了,我就跑,钻进山里,躲进丛林,跟你耗! 利用国土纵深和恶劣气候(尤其是可怕的热带疾病和瘴气),生生把强大的入侵者拖瘦、拖病、拖垮。
等到蒙古军队人困马乏,补给困难,士气低落,不得不撤退时,越南人再瞅准机会,集中优势兵力,在预设的有利战场(比如狭窄的山口、湍急的河流渡口)发动猛烈反击。蒙古重兵集团的优势,在撤退的混乱中根本发挥不出来,反而成了被痛打的落水狗。
所以说,蒙古军队在越南,不是输在不够勇猛,而是输在了极度的“水土不服”。他们那套横扫大陆的战术体系,在越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越南人灵活机动的战术面前,彻底失灵了。
这就像让习惯了冰天雪地的北极熊去热带雨林抓猴子,空有一身力气,却使不上劲,处处挨打。
岭南人,被忽必烈忽略的“通关秘籍”
越南(当时主要指南部的安南、占城等地)和中国的岭南地区(大致是今天的广东、广西、海南一带),在地理、气候、文化上,简直就是亲兄弟。两地山水相连,都受热带、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,夏天湿热多雨,河流纵横,山地丘陵密布。
岭南人几百年来和越南那边打交道,跑商、做官、甚至打仗,对那片土地的门道,摸得门儿清。
忽必烈雄心勃勃要征服南宋时,就有一批有见识的岭南籍官员,比如姚枢、刘整这些人,给蒙古高层提过醒。
他们的核心观点很简单:打南方,特别是打越南这种地方,光靠咱们蒙古铁骑那套不行,得用南方人,尤其是熟悉岭南和安南情况的南方人! 为啥?
懂地形气候: 岭南人知道怎么在湿热环境下行军、扎营、防病。知道哪些季节瘴气最毒,哪些河道雨季会泛滥,哪些山路能走大部队。这些经验,对在越南打仗太重要了。
通语言文化: 岭南和越南语言(古时都属于广义的“百越”语系)有相通之处,习俗也接近。岭南人能当翻译,能搞情报,能招降纳叛,甚至能打入敌人内部搞策反。蒙古人两眼一抹黑,岭南人却能听懂对方的方言土语。
擅水战丛林战: 岭南地区水网密布,山也多。岭南的兵,无论是南宋降兵还是地方武装,熟悉水战,擅长在山地丛林里周旋。这正是蒙古军队在越南最急需补充的短板!让他们当向导,当前锋,打水战,搞丛林袭扰,绝对事半功倍。
可惜啊,忽必烈和他的核心决策圈,一开始根本没把这些“南人”的意见当回事。 蒙古贵族们骨子里带着征服者的骄傲,觉得老子天下第一,横扫欧亚的雄师,打个小越南还不是手到擒来?用那些刚投降的“南蛮子”?靠不住!
而且,蒙古统治者对汉人(尤其是南方的汉人)一直有戒心,怕他们掌握兵权。所以,在前两次大规模入侵越南(1257-1258年,1284-1285年)时,蒙古军队的主力,还是以蒙古、色目(西域各族)精锐为主,北方汉军为辅,真正熟悉南方的岭南籍将领和士兵,很少被委以重任,更别说掌握核心指挥权了。
结果呢?前面一章说了,两次都栽了大跟头!尤其是第二次(1285年),元朝名将唆都率领的大军,中了越南陈朝名将陈兴道的埋伏,在白藤江(历史上有名的战场)几乎全军覆没,唆都本人也战死。
消息传回大都(北京),忽必烈气得差点背过气去。这时候,他才算有点回过味来了,南方的仗,真不是光靠硬弓快马就能打赢的。
白藤江,傲慢付出的血色学费
前两次征越的惨败,特别是第二次(1284-1285年)在白藤江栽的那个惊天大跟头,彻底把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打醒了,也让忽必烈痛彻心扉地明白了什么叫 “轻视南方的代价”。
这场战役,简直就是蒙古军队在越南所有“水土不服”症状的总爆发,也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痛。
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。元朝大将唆都(Sogetu)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水陆大军,一路深入越南腹地,目标直指升龙(今河内)。越南陈朝的兴道大王陈国峻(Tran Hung Dao),这位被越南人尊为军神的统帅,深知硬碰硬就是找死。他玩了一手炉火纯青的 “诱敌深入”加“关门打狗”。
表面上,陈朝军队节节抵抗,不断后撤,把气势汹汹的元军一步步引向预设的死亡陷阱,白藤江口。
白藤江(Bach Dang River)这地方,地理条件极其特殊。它入海口宽阔,但河床底下藏着大片暗滩和沙洲,而且受潮汐影响巨大。涨潮时一片汪洋,水深船高,通行无阻;退潮时水位骤降,暗滩暴露,大船很容易搁浅。岭南籍的降将和水手们,早就提醒过唆都:这地方潮汐规律诡异,河道凶险,必须万分小心,尤其不能在退潮时让大军挤在狭窄江口! 可蒙古统帅们哪听得进“南人”的唠叨?他们被之前的“胜利”冲昏了头脑,觉得越南人不过是手下败将,逃命都来不及,哪敢耍花样?再加上对复杂水文知识的天然轻视,大军就这么一头扎进了陈兴道精心布置的口袋里。
陈兴道的杀手锏,就是“木桩阵”。他趁着退潮,命人在白藤江口关键的浅水区、暗滩上,密密麻麻钉下了成千上万根削尖的巨大木桩!这些木桩大部分藏在水下,涨潮时根本看不见。同时,他在两岸埋伏下精锐部队,只等元军上钩。
1285年4月的那一天,元军庞大的船队(很多还是临时征用或强掠的民船)载着兵马辎重,在退潮前试图通过白藤江口。就在船队主力挤在狭窄江面时,潮水开始急速退去!水位猛降,那些隐藏在水下的致命木桩,像狰狞的獠牙一样露出了水面。
元军的大船小船,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,一艘接一艘狠狠地撞上、卡死在这些尖锐的木桩上!船底被刺穿,船体被牢牢钉在原地,动弹不得。整个江面瞬间乱成一锅粥。
就在元军惊慌失措、进退两难之际,两岸伏兵四起! 越南军队驾着轻便灵活的小船,如狼似虎地扑向搁浅的元军大船。他们用火箭射帆,用长矛钩索登船,与被困在船上的元军展开血腥的接舷战。
同时,岸上的越南步兵万箭齐发,滚木礌石倾泻而下。元军空有强大的骑兵和重兵,在搁浅的船上、在泥泞的岸边,完全成了待宰的羔羊。战马在船上惊恐嘶鸣,士兵在拥挤中自相践踏,加上箭雨火攻,死伤极其惨重。
大将唆都本人,就在这场混乱绝望的战斗中阵亡。元军主力几乎被全歼,只有极少数人侥幸逃脱。白藤江一战,是蒙古帝国扩张史上在东南亚遭遇的最惨烈失败之一,也是陈兴道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。它用鲜血淋漓的事实告诉忽必烈和整个蒙古高层:在南方这片土地上,光靠勇猛和数量,没有对地理、水文、气候的深刻理解,没有善用地利的智慧,再强大的军队也会摔得粉身碎骨! 那些被他们忽略的岭南人的警告,此刻成了最刺耳的嘲讽。
迟来的信任与岭南将星的闪光
白藤江的惨败像一记响亮的耳光,终于把忽必烈打醒了。他意识到,要征服越南这块硬骨头,必须放下征服者的傲慢,学会“以彼之道,还施彼身”。
于是,在筹划第三次(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)征越战争(1287-1288年)时,元朝的用人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
这一次,忽必烈任命自己的儿子镇南王脱欢(Toghon)为总指挥,但真正赋予重任的,是一批经验丰富的岭南籍将领和归附的南宋水军将领。比如:
奥鲁赤(Auruyci):这位色目将领虽非岭南人,但长期在南方作战,经验丰富,更重要的是他开始重视并重用南方汉军。
张文虎:南宋降将,精通水战,被委以水师统帅的重任。
李恒:另一位重要的南宋降将,熟悉南方地形和战法。
以及众多来自广东、广西等地的中下层军官、向导、水手。他们构成了这次远征的核心智囊和前锋力量。
这支混合部队,终于补齐了蒙古军队在越南战场最致命的短板。
强大的水师: 吸取了白藤江的教训,这次元朝组建了一支真正强大的舰队。这支舰队由张文虎等南方将领指挥,士兵也多是熟悉水性的南方人。他们不仅能保障后勤运输,更能直接投入水战,争夺关键水道控制权。
丛林向导与情报网: 岭南籍的士兵和向导,利用语言、习俗相近的优势,深入敌后或混入当地,搜集情报,甚至策反部分越南地方势力。他们对热带丛林行军、防病、寻找水源和路径的经验,极大地减少了非战斗减员。
灵活的地面战术: 在岭南将领的参与和影响下,元军的地面部队不再一味追求大规模骑兵冲击,而是学会了组建更灵活的步兵分队,适应丛林和山地作战,并尝试与越南军队进行小规模的袭扰和反游击。
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
第三次征越初期,元军进展比前两次顺利得多。水陆并进,势如破竹。强大的水师保障了后勤(虽然压力依然巨大),地面部队在熟悉地形的岭南向导带领下,避开了不少陷阱,有效打击了越南军队。1288年初,元军甚至再次攻占了升龙(河内)。看起来,胜利似乎就在眼前。
然而,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,当你以为找到了钥匙,锁眼却可能已经换了位置。
元军的战术进步了,但他们的对手陈兴道,更是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大师。他再次祭出了对付蒙古人的终极法宝:坚壁清野 + 持久消耗 + 伺机反击。
越南军民将粮食藏入深山,水源投毒,留给元军的是一座座空城和焦土。庞大的元军(据说超过三十万,数字或有夸大,但规模肯定巨大)困在湿热、疾病肆虐的异国他乡,后勤补给线拉得极长,即使有水师也难以为继。
饥饿和疾病,这个蒙古军队在越南永远的噩梦,再次悄然降临。士兵大量病倒,士气低落。
与此同时,陈兴道耐心地等待时机。他敏锐地发现,元军虽然战术有所改进,但其庞大臃肿的体量、对后勤的极度依赖以及最高决策层(脱欢)可能存在的经验不足和内部矛盾,依然是致命的弱点。他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,静静地等待猎物露出疲态。
最终的结局,竟惊人地像是白藤江的翻版,只是地点换在了另一条关键水道,云屯(Van Don)海域。
1288年3月,元军庞大的运粮船队在云屯海面,再次被陈兴道抓住潮汐和地形的时机,利用火攻和小船突击,配合岸上伏兵,重创了元军后勤舰队!大量宝贵的粮草被焚毁或沉入大海。这个消息,对于已经陷入困境的前线元军来说,无异于晴天霹雳。
后勤命脉被切断,前线军队饥病交加,士气彻底崩溃。 镇南王脱欢眼看胜利无望,再拖下去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,只得在占领升龙仅仅几个月后,就灰溜溜地下令撤军。撤退途中,又不断遭到越南军队的追击和袭扰,损失惨重。
第三次声势浩大的征越战争,最终仍以元朝的失败撤退告终。
岭南人的智慧虽然带来了战术上的改进,一度取得进展,却终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蒙古帝国在越南面临的结构性困境。
忽必烈至死也没能圆他的“安南梦”。
三次大规模远征,耗费了帝国无数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损兵折将,最终却只换来越南陈朝名义上的“臣服”(实际保持高度独立)。越南,成了蒙古铁蹄下少数几个成功捍卫了自身独立的国家之一,这份荣耀至今被越南人铭记。
晚年的忽必烈,据说常常对着南方地图长吁短叹。史料虽未明言,但从他后期对南方事务的反思和对岭南籍官员的有限重用来看,他内心深处恐怕确实充满了悔意。
他或许终于明白了:横扫欧亚大陆的无敌战法,在热带雨林、密布河网和坚韧的人民意志面前,是有极限的。
他后悔的,不仅是“不用岭南人”的战术失误,更深层的,或许是蒙古帝国那种高度依赖草原骑兵优势、相对轻视地方复杂性和适应性治理的统治逻辑,在面对像越南这样具有独特地理文化禀赋的地区时,暴露出了根本性的不适应。
发布于:江西省股票开通杠杆.中国正规股票app排名.网上股票杠杆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